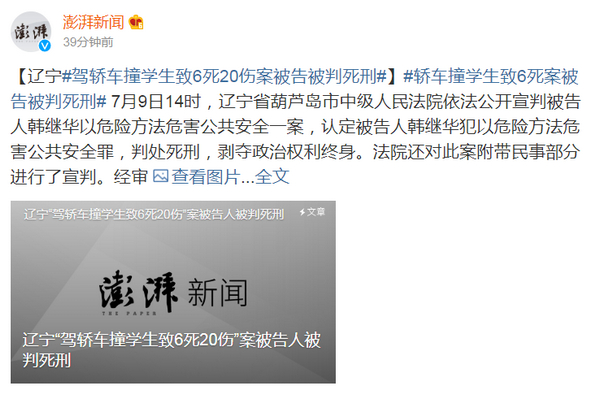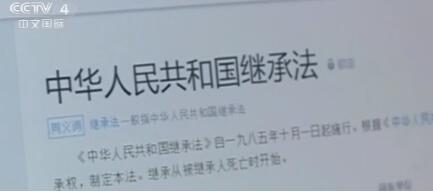回忆中苏友好岁月
解放后我升入杭州高中,当时报纸上都说苏联是我们老大哥,中苏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国际关系,是马列主义政党的同志真诚关系,会友好万万年,我们学生也就相信了。 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高
解放后我升入杭州高中,当时报纸上都说苏联是我们老大哥,中苏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国际关系,是马列主义政党的同志真诚关系,会友好万万年,我们学生也就相信了。
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高尔基三部曲、米丘等我们都很爱看。中苏友协组织苏联电影之友,加入了发张卡,看一场电影只要五分钱,同学们纷纷加入。很快,原来的基督教青年会改成展览馆,有大量主题展览,如苏联的集体农庄生活、克里姆林宫介绍、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庄园等,我们高中生没有见过世面,对这些外国风光感到新奇。
不久,苏联的红旗歌舞团、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接连到访,战士们蹲着马步踢腿的矫健英姿使我们大开眼界。
一九五二年史达林突然去世,我们感到震惊,杭州在宽阔的延龄路上举行全市追悼大会,大家为伟人的去世深感悲痛,接任的马林科夫好像也很英明。
一九五三年我调干上大学,就选定俄语专业。这时中苏友谊大厦刚落成,我们去参观;苏联的年轻讲解员说着流利的汉语,读出廊柱上的中文标语,我们惊讶地直吐舌头。这时红梅花儿开等歌曲传遍中国,我们在大学里读俄语、说俄语、唱俄语歌、跳俄国集体舞,中苏友好又掀起高潮。
但不久老革命贝利亚被处死,马林科夫靠边站,赫鲁雪夫冒出来;他去美国,在联合国大会脱了皮鞋敲讲台,他列举史达林杀戮对手的事实使我们感到匪夷所思。苏联的伟大在我们心目中打了折扣。
我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分派到陕北米脂中学教俄语。我热情地教,学生们努力学。一九五七年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国内热烈庆祝,伏罗希洛夫访华,报上尊称他伏老,又掀起友好热潮。
我在北京友好报用俄文发表文章,描述我的学生努力学习俄语的情景,收到苏联各地寄来的一百多封来信,纷纷表示友好和支持。我发动学生开展和苏联学生的友好通信,提高了俄语学习效果,高考俄语成绩全省第一。
当时国内平信邮资八分,寄到苏联要两角二,学生们仍凑钱寄信。学生毕业后多人投考外语学院,陕北考区的学生成分好,毕业后多人成驻东欧外交官。
不久传言中苏有了分歧,我一点也不信,我认为有共同信仰的马列主义政党怎么可能有分歧。
六○年代初,论战公开,一评、二评直至九评,大力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我也不敢再和苏联朋友通信了,就这样,文革时仍被造反派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没有多久,永远友好的同盟成了冤仇,甚至兵戎相见。随后,又出现一系列新盟友,有血肉凝成的、有并肩战斗的、有互相支持的;特别是欧洲的一盏明灯意外地坚定,一百万人口的小国,支援的物资吃不完用不完,拖拉机烂在地里。时局一变,新盟友又和我们横眉冷对,一个接一个,接二连三,都说自己掌握正义,对方是犹大。
美帝的头头却意外到访北京,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斯诺被请上天安门,出现中美友好的新趋势,学校里的俄语课都改成英语,学Follow Me成了新时髦,世界的演变真是我们普通人料想不到。
俱往也, 看来国际交流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存在的只是利益。一个时期响亮的口号,到另一个时期便不合时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才是不变的真理。
-

-
 哈根达斯60周年庆生活动 一勺奢宠 至简不凡2020-10-27(2020年10月27日,中国·上海) 双节假期刚尽,秋韵浓厚。哈根达斯作为行业领头者,在上海古北财富新店举办了60周年庆生下午茶媒体活动 。古北财富店秉承品牌经典、演绎
哈根达斯60周年庆生活动 一勺奢宠 至简不凡2020-10-27(2020年10月27日,中国·上海) 双节假期刚尽,秋韵浓厚。哈根达斯作为行业领头者,在上海古北财富新店举办了60周年庆生下午茶媒体活动 。古北财富店秉承品牌经典、演绎 -
 压力催人老?Skin Regimen小黑瓶肌底液解救“秋冬压力肌”就现在2020-10-27压力催人老?Skin Regimen小黑瓶肌底液解救“秋冬压力肌”就现在 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快,同时城市污染也越发严峻,身心健康都受到巨大威胁的同时,肌肤的问题也随之频
压力催人老?Skin Regimen小黑瓶肌底液解救“秋冬压力肌”就现在2020-10-27压力催人老?Skin Regimen小黑瓶肌底液解救“秋冬压力肌”就现在 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快,同时城市污染也越发严峻,身心健康都受到巨大威胁的同时,肌肤的问题也随之频 -

-
 传承匠心之魂!G-SHOCK冲击丸限量问世,锻錾不朽甲胄2020-10-26甲胄作为日本手作技艺的旷世传奇,其精湛工艺令人叹为观止,拥有无法估量的艺术收藏价值。G-SHOCK旗下顶上之工艺腕表MR-G系列以日本传统Kabuto(头盔)为灵感,融合日本传统美
传承匠心之魂!G-SHOCK冲击丸限量问世,锻錾不朽甲胄2020-10-26甲胄作为日本手作技艺的旷世传奇,其精湛工艺令人叹为观止,拥有无法估量的艺术收藏价值。G-SHOCK旗下顶上之工艺腕表MR-G系列以日本传统Kabuto(头盔)为灵感,融合日本传统美 -
 秋季防晒不容忽视 FFLOW精油水防晒隔离霜助你打造通透素颜妆2020-10-26随着秋季的到来,天气逐渐转凉,温度的下降让有些小仙女开始忽视防晒。殊不知,秋季阳光斜射,虽然紫外线在日光中的含量明显下降,但云层稀薄,天气干燥,紫外线更容易穿透皮肤刺
秋季防晒不容忽视 FFLOW精油水防晒隔离霜助你打造通透素颜妆2020-10-26随着秋季的到来,天气逐渐转凉,温度的下降让有些小仙女开始忽视防晒。殊不知,秋季阳光斜射,虽然紫外线在日光中的含量明显下降,但云层稀薄,天气干燥,紫外线更容易穿透皮肤刺 -
 秋季必备保湿补水面膜FFLOW精油水镇定&提亮面膜2020-10-26秋季到了,天气逐渐转凉,肌肤的水分流失容易出现细纹、粗糙、角质化等现象,室内与室外的温差变化会促使肌肤疲劳,新陈代谢的功能衰退,皮肤会变得暗淡无光。秋季补水,使用FFL
秋季必备保湿补水面膜FFLOW精油水镇定&提亮面膜2020-10-26秋季到了,天气逐渐转凉,肌肤的水分流失容易出现细纹、粗糙、角质化等现象,室内与室外的温差变化会促使肌肤疲劳,新陈代谢的功能衰退,皮肤会变得暗淡无光。秋季补水,使用FFL -

-
 水之密语“净水计划”远赴贵州毕节,爱心“小水滴”伴你成长!2020-10-23作为资生堂集团旗下的高档洗护品牌,水之密语在关注中国女性秀发和身体水润需求的同时,更肩负着品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助力公益,希望通过改善喝水这件‘小事’,
水之密语“净水计划”远赴贵州毕节,爱心“小水滴”伴你成长!2020-10-23作为资生堂集团旗下的高档洗护品牌,水之密语在关注中国女性秀发和身体水润需求的同时,更肩负着品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助力公益,希望通过改善喝水这件‘小事’, -
 蕾美缪思拉多芮腮红小课堂:缤纷腮红黄皮怎么选才显白2020-10-22进入秋冬季节之后,很多女生的衣柜又变回了经典的黑白灰以及驼色、卡其色等大地色系,整体色调与春夏季节相比稍显单一、沉闷。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个人魅力、凸显好气色,很
蕾美缪思拉多芮腮红小课堂:缤纷腮红黄皮怎么选才显白2020-10-22进入秋冬季节之后,很多女生的衣柜又变回了经典的黑白灰以及驼色、卡其色等大地色系,整体色调与春夏季节相比稍显单一、沉闷。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个人魅力、凸显好气色,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