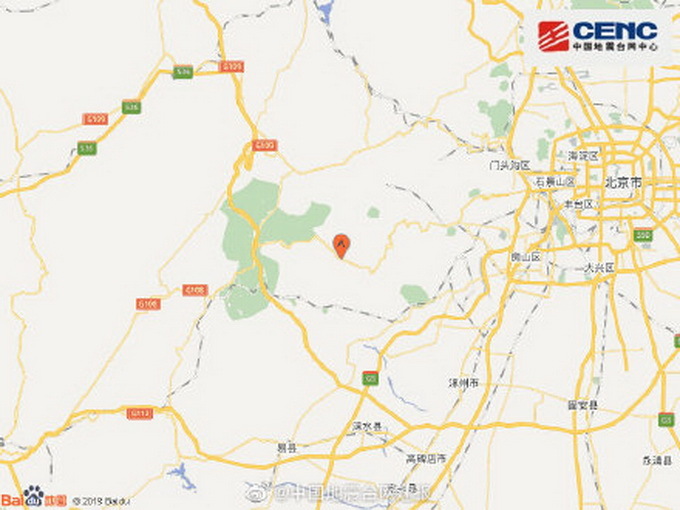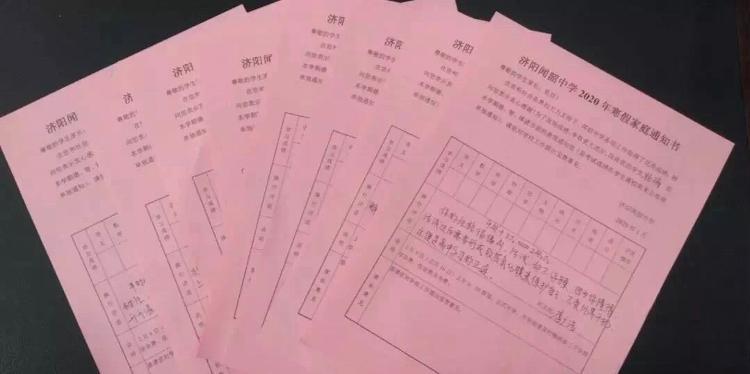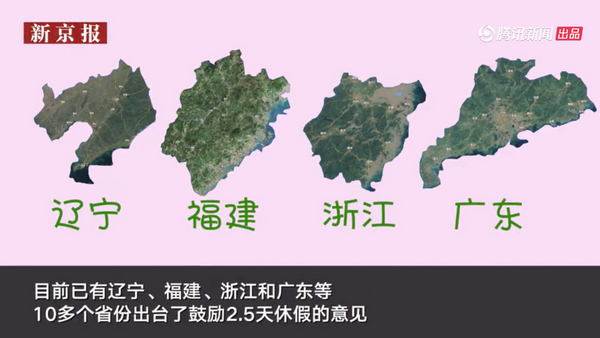进山挖葛根
儿子在超市给我买来葛粉,说是给我补充营养,一大盒精装的五百克葛粉,花了八十五元。盒子上还写着北有人参,南有葛根、圆梦野生葛粉,有的还标上野山净土,自然天成等等美丽的语言。
儿子在超市给我买来葛粉,说是给我补充营养,一大盒精装的五百克葛粉,花了八十五元。盒子上还写着北有人参,南有葛根、圆梦野生葛粉,有的还标上野山净土,自然天成等等美丽的语言。如此珍贵的葛粉,让我惊愕了。
回想我们苦日子进山挖葛根,并没有人认为如何珍贵;那时是因为粮食定量不够,百姓挖葛根都是为了补充粮食。过苦日子以前,山民挖葛根是为挣点盐钱,集市上的葛粉卖三角钱一斤,山里到处都有,太不值钱了;如今儿孙们听了这些,羡慕我们苦日子还有福气吃补品。
深秋和立冬前,山里的葛根正值根壮多粉,当年每到周日,我和邻居同学加入城里大人们的队伍,有休息天的工人、居民和各行各业的人,有的一家大小,背着竹筐,扛着挖锄,带上几个红薯当中餐,进山挖葛根。有时妈妈也同我们一起进山,那时挖葛根的场景很热闹又壮观,现在山林里见不到那样的场面了。
挖葛根时,妈妈说要寻找那些粗的葛根,出的葛粉才多。可是小镇周围山林里细小的葛根都被挖完了,哪里还有粗壮的葛根呢。于是,要走很远的山坡路,进到高山深林里去,才有机遇找到粗的葛根。有的大妈大嫂们走不了远山路,就在附近林子里挖一种蕨根,就是山上蕨菜的根,蕨根粉似葛粉,但做出的食品叫「蕨粑」,口感比葛粉细滑柔韧,有一股山野的清香;最粗壮的蕨根也只有筷子粗,出粉量很低,集市上也只卖五角钱一斤。现在山里哪还有野生的蕨和葛?大片人工种植的,一经宣传包装,价钱飞上了几十倍。
我们小镇位于湘西雪峰山下,最初,我们只在山下的一些灌木树林里找葛根,当发现一大片茂盛的葛藤叶时,不知葛根藏在哪里,无法找到。我们就用毛镰刀,从脚旁一阵砍伐,砍出一片空地,把那些绊手绊脚的藤蔓藤叶都砍光了,才找到葛根的部位,再顺藤理去,用锄一下一下地往深处挖根。
挖的人太多了,一座山林,几天就被我们挖光。山民说藤细小的是柴葛,我们也不懂什么叫柴葛,只是很高兴地挑着葛根回到家,已经是太阳西下了。同我们一起去的邻里们,也都挑着葛根,挑着一天寻粮的希望回家了。
一大堆淡黄色的葛根像柴棍样,第二天,大家忙着槌葛根,在我们十多家共用的一个大厨房里,像手工作坊一样,一声接一声的槌葛根声响起一大片。
那时家庭没有磨浆机,只得把洗干净的葛根剁成小节,放在木盆里用木槌捶碎,直到捶出灰白色的葛浆。也有的拿到郊区农民家,借用石臼捣烂后,再拿回家用水洗泡、白布过滤几次,最后沉淀出洁白的葛粉块。
那天,我和妈妈挖了二十多斤柴葛根,累了一天,才加工出二斤多湿葛粉。当年家庭妇女的粮食定量由二十四斤减少到二十二斤,我是高中生,每月定量三十六斤,家里还有弟妹,粮食不够吃。每个周日,我都要进山去挖葛。妈妈辛苦滤出的葛粉,做好一个个喷香的葛粑,自己只尝一口,就分给我们吃了。妈妈说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了肚子。
苦日子的第二年,城里进山挖葛的愈来愈多了,近处的山没有挖的了。一次,我跟着几位工人同伴和邻里陈大哥,过山界穿密林,到了雪峰山坳的一个老山林里,在林子深处的岩坎旁,长满了古树枯藤,阴森森的,天空的阳光也射不进;我终于发现一棵比拇指粗的老藤盘缠在另一棵老树上,碧绿绿的长圆形叶,我一眼认出那是一株老葛根。
我高兴地叫来了陈大哥和同伴,都说是多年生的粉葛,在大家合作下,挖出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葛根近百斤。
我分得了一根最粗的葛根,有二十多斤,比大人的拳头还粗,还有不少小根的。回到家,邻里们都为我惊喜,因为老葛含淀粉多,生吃很甜香。妈妈当即用刀切下厚厚的一片片,分享给围观的邻里,大家高兴地说,也要进深山去寻找葛根。那次我们还捶制出四斤多葛粉块。
如今的山里,很难有那样的野生葛了,回忆往日进山挖葛根,我们的福气不仅是享受到真正的野生葛清香,而最大的补品是在困苦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
 扎根护肤市场7年,典萃终于迎来高光时刻2020-11-13在科技类、功能型护肤品需求日趋增加的当下,许多美妆品牌都开始探索科技护肤这片红海。典萃作为上海家化旗下的美妆护肤品牌,历经7年探索和沉淀,于2020年成功升级,正式对外
扎根护肤市场7年,典萃终于迎来高光时刻2020-11-13在科技类、功能型护肤品需求日趋增加的当下,许多美妆品牌都开始探索科技护肤这片红海。典萃作为上海家化旗下的美妆护肤品牌,历经7年探索和沉淀,于2020年成功升级,正式对外 -
 rorolove携手宋祖儿探索方寸之间的女性魅力2020-11-13她是《宝莲灯前传》里疾恶如仇的哪吒,她是九州缥缈录里美貌机智的羽然公主,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祖鹅”,她就是宋祖儿。近日,rorolove携手宋祖儿登上《NEUFMODE九号摩
rorolove携手宋祖儿探索方寸之间的女性魅力2020-11-13她是《宝莲灯前传》里疾恶如仇的哪吒,她是九州缥缈录里美貌机智的羽然公主,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祖鹅”,她就是宋祖儿。近日,rorolove携手宋祖儿登上《NEUFMODE九号摩 -
 业态创新 模式升级 Brand K直播带货迎战“双11”2020-11-1211月11日,电商平台“消费狂欢”高潮迭起。在这场“双11”购物盛宴中,Brand K以新兴业态“网红直播带货”的方式,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多品类
业态创新 模式升级 Brand K直播带货迎战“双11”2020-11-1211月11日,电商平台“消费狂欢”高潮迭起。在这场“双11”购物盛宴中,Brand K以新兴业态“网红直播带货”的方式,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多品类 -
 1.28亿!碧生源打造双十一健康盛宴 瘦身C位好物全网热销2020-11-12上半年疫情封印,让2020下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来得更加猛烈。直播带货线上火热“种草”,好物应接不暇,全网都是停不下来的买买买。受疫情驱动和公众消费理念提升
1.28亿!碧生源打造双十一健康盛宴 瘦身C位好物全网热销2020-11-12上半年疫情封印,让2020下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来得更加猛烈。直播带货线上火热“种草”,好物应接不暇,全网都是停不下来的买买买。受疫情驱动和公众消费理念提升 -
 如何与年轻人沟通?自然堂开办“支流大学”强势出圈2020-11-11年轻人的身上藏着一股独一无二的力量,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与自我,就像一条奔涌向前、充满热情的支流。然而就是这样各有风彩的年轻人,却总是因这份独有的不同而陷入社会各界的
如何与年轻人沟通?自然堂开办“支流大学”强势出圈2020-11-11年轻人的身上藏着一股独一无二的力量,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与自我,就像一条奔涌向前、充满热情的支流。然而就是这样各有风彩的年轻人,却总是因这份独有的不同而陷入社会各界的 -
 博物馆奇妙夜 ——JI CHENG 2021SS“鲤花”系列发布即将上线2020-11-10当夜幕降临魔都的黄浦江畔,奇妙空间被神秘能量开启,2020年11月16日,一场艺术情境中的视觉感官盛宴即将在Teamlab无界美术馆上演,中国著名独立时装设计师吉承怀抱对艺术的热
博物馆奇妙夜 ——JI CHENG 2021SS“鲤花”系列发布即将上线2020-11-10当夜幕降临魔都的黄浦江畔,奇妙空间被神秘能量开启,2020年11月16日,一场艺术情境中的视觉感官盛宴即将在Teamlab无界美术馆上演,中国著名独立时装设计师吉承怀抱对艺术的热 -
 坚韧进化,自成风度!G-SHOCK MT-G系列演绎进无止境2020-11-06跨越指针转动的风尚型格,是理想与时间的经年对谈。创造超越潮流的硬朗表达,是男士魅力的铮铮信条。这一次,G-SHOCK将MT-G产品线再度升级进化,在MTG-B1000基础上,全新推出MT
坚韧进化,自成风度!G-SHOCK MT-G系列演绎进无止境2020-11-06跨越指针转动的风尚型格,是理想与时间的经年对谈。创造超越潮流的硬朗表达,是男士魅力的铮铮信条。这一次,G-SHOCK将MT-G产品线再度升级进化,在MTG-B1000基础上,全新推出MT -
 双十一必buy清单 飘柔让秋冬护发尽享柔顺体验2020-11-05又逢双十一,你是否已经摩拳擦掌,做好准备买买买了?在绞尽脑汁计算凑单优惠的时候,肯定也在默默蹂躏自己的头发。说到头发护理,做好清洁是最基础的,但天气渐冷,正逢没有暖气的保护,
双十一必buy清单 飘柔让秋冬护发尽享柔顺体验2020-11-05又逢双十一,你是否已经摩拳擦掌,做好准备买买买了?在绞尽脑汁计算凑单优惠的时候,肯定也在默默蹂躏自己的头发。说到头发护理,做好清洁是最基础的,但天气渐冷,正逢没有暖气的保护, -
 优衣库携+J首次亮相进博会,演绎当代科技极简美学2020-11-052020年11月5日至10日,全球知名服饰品牌优衣库惊艳亮相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1500平方米“明日博物馆”。这是优衣库LifeWear全球品牌博览会继纽约、
优衣库携+J首次亮相进博会,演绎当代科技极简美学2020-11-052020年11月5日至10日,全球知名服饰品牌优衣库惊艳亮相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1500平方米“明日博物馆”。这是优衣库LifeWear全球品牌博览会继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