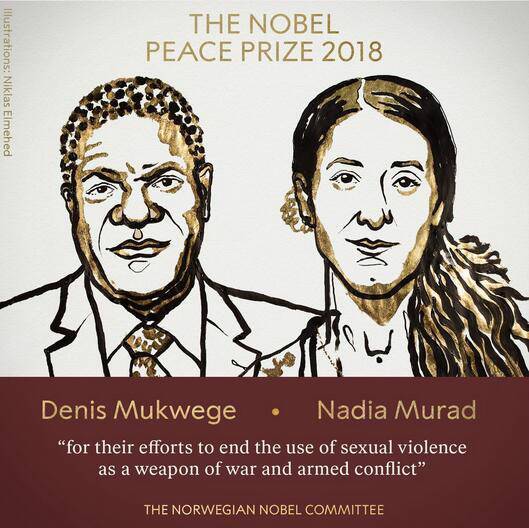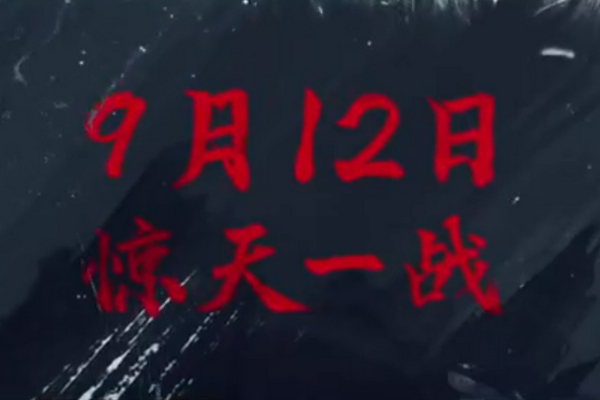《老照片说故事》三十年追思
这张照片是三十年前回嘉兴老家探亲时,我太太为我们姊弟三人拍摄的。图中我脚踩故乡的庄稼地,背后是乡亲们的幢幢新楼,紧依着久未谋面的老姊老哥,乡情亲情融于一框,何况这还是我
这张照片是三十年前回嘉兴老家探亲时,我太太为我们姊弟三人拍摄的。图中我脚踩故乡的庄稼地,背后是乡亲们的幢幢新楼,紧依着久未谋面的老姊老哥,乡情亲情融于一框,何况这还是我们几十年来的第一张合照,我一直珍藏着。今天重新审视,欣喜和悲怆之情一并涌上心头。
我在家乡读完小学,就外出继续求学,接着在外转辗工作,其间鲜少返家。随着年龄增长,思乡之情常萦绕于心;于是一九九一年二月寒假期间,我偕同太太回乡探亲过年。屈指算来,离乡已有整整四十五个年头。
我父母早年先后亡故,大姊因患血吸虫病壮年逝去,二姊则远嫁嘉善县,现时老家只有哥哥一脉。那天哥哥和侄儿在村口车站迎接。到家后在堂屋坐定,喝茶聊天;未几,旧时亲友、儿时玩伴闻讯而来,把堂屋挤得满满的,大家亲热地寒喧叙旧,都很开心。
午后二姊特地从外县赶来,我们三个六、七十岁的老姊弟久别重聚,相拥相依,喜出望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儿时的记忆像打开闸门的水一样奔涌而出。
我三岁那年母亲去世,我们姊妹兄弟四人顿时成了没娘的孩子。因父亲需全力打理药店业务,十五岁的大姊挑起家务重担,大我十岁的二姊则特别关照我这个稚幼的小弟。我四岁那年出痧症,高烧三天,她整天看护我,陪我说话、喂汤药、擦汗换衣,十三、四岁的她像是我的小妈妈。
我五岁时嘉兴沦陷,白天日军隔三差五地来镇上抢东西、抓花姑娘;晚上盗贼横行,入村劫户。每当我们听闻「日本兵来了」或「强盗来了」的喊声时,立时关上大门,带上装着细软的逃难包,迅速从后门逃出,白天去邻村朋友家,晚上就在田间林地、坟头暂避。凡是这种时候,多是二姊抱或者背着我逃跑。尤其冬天夜晚在坟墓旁久待,又怕又冷,二姊把我紧抱胸前,为我壮胆取暖。
她成年后嫁去邻县,因姊夫家被划为地主成分,扫地出门,全家挤在一个破庙中,过着居不挡雨、食不果腹的生活。更不幸的是,当小学老师的姊夫又先她而去,家中失去栋梁,在这种艰难境遇下,她苦苦撑住,把二个外甥、三个甥女带大。
哥哥大我五岁,从小就是我的领头羊,我常跟着他东跑西走,他说我是跟屁虫。我五岁时跟着他读私塾,学他摇头晃脑地读经背书;次年村里起洋学堂,我又天天背起小书包跟着他上学,一起读书、写字。
稍长他在自家药店学做生意,我就到店堂去跟他玩。哥哥记性好,一本汤头歌诀背得滚瓜烂熟。他手也巧,刻花、刻字、刻印章,如过年门上的贴花纸、做松糕的印板,乃至私人印章,样样都会。我也跟着他在蜡盘上刻镂空花纸,做成贺年卡送给同学;他教我在毛竹筒一边刻着竹叶,另一边刻上龙飞凤舞四字,作为笔筒。他象棋下得好,我从小就跟他下棋,他让我车马二子,我都赢不了他。在他的影响下,我养成了喜好动脑动手的习惯。
那个春节我们一起度过三天三晚,好似有说不完的话语、讲不尽的故事。几年后,我和太太移居美国,我们仍每二年回国探亲。
二○一三年五月我刚回国探望过他们,岂料当年十一月不幸消息传来,哥哥因癌症晚期发作,已经病危。我急挂越洋电话去他的病房,他打起最后的精神和我通话,痛苦地讲述他的病况,透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我不禁悲从中来,哽咽失声。两天后哥哥与世长辞,时年八十五岁。我和他弥留之际的电话对话,竟成最后的诀别。
二○一八年二月外甥发来微信,九十五高龄的二姊摔跤后卧床不起。又二月余,他发来视频,但见她在病塌上渐渐停止呼吸,溘然长逝。我看着心如针刺,潜然泪下。
三十年前我们姊弟三人欢聚合影的记忆犹新,可叹如今他们二人已然离去,再见无期,只留下无尽的思念。
-
 扎根护肤市场7年,典萃终于迎来高光时刻2020-11-13在科技类、功能型护肤品需求日趋增加的当下,许多美妆品牌都开始探索科技护肤这片红海。典萃作为上海家化旗下的美妆护肤品牌,历经7年探索和沉淀,于2020年成功升级,正式对外
扎根护肤市场7年,典萃终于迎来高光时刻2020-11-13在科技类、功能型护肤品需求日趋增加的当下,许多美妆品牌都开始探索科技护肤这片红海。典萃作为上海家化旗下的美妆护肤品牌,历经7年探索和沉淀,于2020年成功升级,正式对外 -
 rorolove携手宋祖儿探索方寸之间的女性魅力2020-11-13她是《宝莲灯前传》里疾恶如仇的哪吒,她是九州缥缈录里美貌机智的羽然公主,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祖鹅”,她就是宋祖儿。近日,rorolove携手宋祖儿登上《NEUFMODE九号摩
rorolove携手宋祖儿探索方寸之间的女性魅力2020-11-13她是《宝莲灯前传》里疾恶如仇的哪吒,她是九州缥缈录里美貌机智的羽然公主,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祖鹅”,她就是宋祖儿。近日,rorolove携手宋祖儿登上《NEUFMODE九号摩 -
 业态创新 模式升级 Brand K直播带货迎战“双11”2020-11-1211月11日,电商平台“消费狂欢”高潮迭起。在这场“双11”购物盛宴中,Brand K以新兴业态“网红直播带货”的方式,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多品类
业态创新 模式升级 Brand K直播带货迎战“双11”2020-11-1211月11日,电商平台“消费狂欢”高潮迭起。在这场“双11”购物盛宴中,Brand K以新兴业态“网红直播带货”的方式,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多品类 -
 1.28亿!碧生源打造双十一健康盛宴 瘦身C位好物全网热销2020-11-12上半年疫情封印,让2020下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来得更加猛烈。直播带货线上火热“种草”,好物应接不暇,全网都是停不下来的买买买。受疫情驱动和公众消费理念提升
1.28亿!碧生源打造双十一健康盛宴 瘦身C位好物全网热销2020-11-12上半年疫情封印,让2020下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来得更加猛烈。直播带货线上火热“种草”,好物应接不暇,全网都是停不下来的买买买。受疫情驱动和公众消费理念提升 -
 如何与年轻人沟通?自然堂开办“支流大学”强势出圈2020-11-11年轻人的身上藏着一股独一无二的力量,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与自我,就像一条奔涌向前、充满热情的支流。然而就是这样各有风彩的年轻人,却总是因这份独有的不同而陷入社会各界的
如何与年轻人沟通?自然堂开办“支流大学”强势出圈2020-11-11年轻人的身上藏着一股独一无二的力量,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与自我,就像一条奔涌向前、充满热情的支流。然而就是这样各有风彩的年轻人,却总是因这份独有的不同而陷入社会各界的 -
 博物馆奇妙夜 ——JI CHENG 2021SS“鲤花”系列发布即将上线2020-11-10当夜幕降临魔都的黄浦江畔,奇妙空间被神秘能量开启,2020年11月16日,一场艺术情境中的视觉感官盛宴即将在Teamlab无界美术馆上演,中国著名独立时装设计师吉承怀抱对艺术的热
博物馆奇妙夜 ——JI CHENG 2021SS“鲤花”系列发布即将上线2020-11-10当夜幕降临魔都的黄浦江畔,奇妙空间被神秘能量开启,2020年11月16日,一场艺术情境中的视觉感官盛宴即将在Teamlab无界美术馆上演,中国著名独立时装设计师吉承怀抱对艺术的热 -
 坚韧进化,自成风度!G-SHOCK MT-G系列演绎进无止境2020-11-06跨越指针转动的风尚型格,是理想与时间的经年对谈。创造超越潮流的硬朗表达,是男士魅力的铮铮信条。这一次,G-SHOCK将MT-G产品线再度升级进化,在MTG-B1000基础上,全新推出MT
坚韧进化,自成风度!G-SHOCK MT-G系列演绎进无止境2020-11-06跨越指针转动的风尚型格,是理想与时间的经年对谈。创造超越潮流的硬朗表达,是男士魅力的铮铮信条。这一次,G-SHOCK将MT-G产品线再度升级进化,在MTG-B1000基础上,全新推出MT -
 双十一必buy清单 飘柔让秋冬护发尽享柔顺体验2020-11-05又逢双十一,你是否已经摩拳擦掌,做好准备买买买了?在绞尽脑汁计算凑单优惠的时候,肯定也在默默蹂躏自己的头发。说到头发护理,做好清洁是最基础的,但天气渐冷,正逢没有暖气的保护,
双十一必buy清单 飘柔让秋冬护发尽享柔顺体验2020-11-05又逢双十一,你是否已经摩拳擦掌,做好准备买买买了?在绞尽脑汁计算凑单优惠的时候,肯定也在默默蹂躏自己的头发。说到头发护理,做好清洁是最基础的,但天气渐冷,正逢没有暖气的保护, -
 优衣库携+J首次亮相进博会,演绎当代科技极简美学2020-11-052020年11月5日至10日,全球知名服饰品牌优衣库惊艳亮相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1500平方米“明日博物馆”。这是优衣库LifeWear全球品牌博览会继纽约、
优衣库携+J首次亮相进博会,演绎当代科技极简美学2020-11-052020年11月5日至10日,全球知名服饰品牌优衣库惊艳亮相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1500平方米“明日博物馆”。这是优衣库LifeWear全球品牌博览会继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