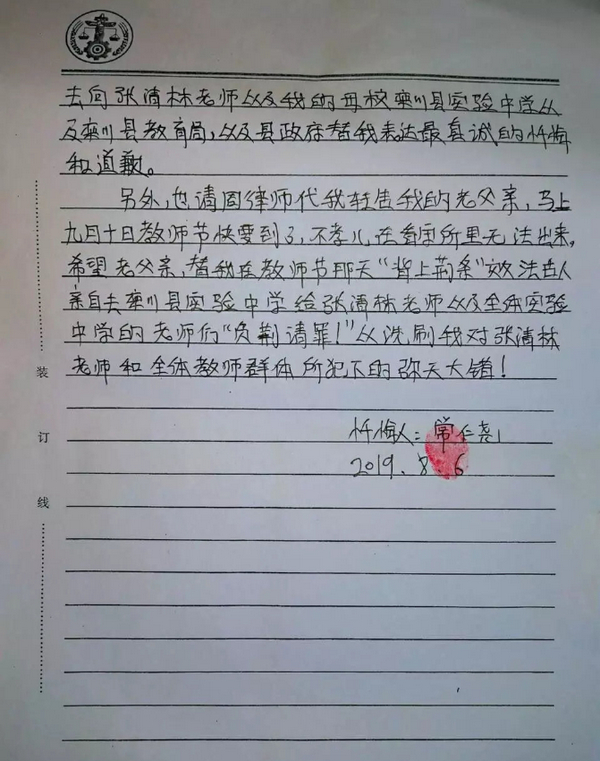相约看烟花
同于梨华大姐的半生交往, 皆缘自于天时地利互相配合。年轻时,她和我都在美国东岸待过,她的先生在纽约州立大学教物理,于大姐那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人生也正在蜕变中,由少
同于梨华大姐的半生交往, 皆缘自于天时地利互相配合。年轻时,她和我都在美国东岸待过,她的先生在纽约州立大学教物理,于大姐那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人生也正在蜕变中,由少妇逐渐进入中年,而且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令人赞赏的以留学生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和她谈话中可以听得出来她有点郁闷,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心态,隐隐地怀着不满和反叛的复杂心理,我那时就感觉到她极力想要突破自己的局限,创造一种新的模式或发展新的内容题材。她似乎特别喜欢与年龄比她年轻一辈的人来往,大概与她那时候心理的需求有关系吧。林怀民那时候正在纽约习舞,也是她的年轻朋友之一。
那时候初初认识她,整天听到她总是嘻嘻哈哈,笑声朗朗,也很喜欢开朋友的玩笑。大概有时电话太多,电话铃声一响,她拿起电话来,对着电话便大声叫嚷起来,先不问对方是谁,却问“What do you want?" 搞得来电话的人不知所措,我看在眼里,觉得怪好笑的。
她喜欢调侃人家,人家也会回敬她一招。记得有次朋友在纽约汇聚,余光中老师也在场,我们几个人被安排住在大姐家,翌日,余老师一边搜索冰箱,一边调侃着大姐:「梨华,你们家的冰箱,我看好像是我所见过的最贫瘠的冰箱嘛,简直没东西可吃哩!」于姐好像不大好意思的样子,但仍不甘心认输回答:「说嘛,你想吃什么?」于姐就是这么率真、大剌剌的人,她似乎不怎么在意人家说她什么,除非你批评她的作品,所以,与她相处的时光里,总是笑的时间多。
2000千禧年那年,海外华文女作家在东岸北卡举行双年会,那次有好几位前辈女作家到场,有齐邦媛教授专题演讲,记得那天不知何故矛头转向于姐而来,许多作家认为于梨华那几年的作品过份着重有关性欲的书写,有人觉得写得太露骨,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于大姐则坚持写作必须诚实的理念,极力为她自己申辩,她认为身为作家,必须为社会上不敢大胆正视的问题发声,不平则鸣。于姐的性格本来就存有反抗的因数,她喜欢让人惊奇,为了表现她的勇敢不羁,更为了求新求变,她甚至不顾挺而走险。好在她悬崖勒马,没继续冲下崖去。其实她应该感谢这些文学姐妹们的。
我们在东岸麻州只待了一年多便离开了。我们先去了西雅图一住十年,再见到于姐之时,已经过了十二个寒暑,此时我已蜕变成了单身;于姐银发期时又作了一次新嫁娘,嫁给了纽约州立大学的校长奥莱瑞先生。
1989年夏天,我听说他们俩人将到西海岸来度蜜月,并至旧金山的东方书店签名销书,她那时的新作好像是《傅家的儿女》。我特意开车前往,要给他们一个惊喜。记得当天阳光明媚,于姐更是春风满面,我们在书店里聊了好一会儿,谈及当年种种,无限沧桑,不禁一再唏嘘。这时于姐的孩子气却又来了,不停地问我:
「妳觉得他(她的新夫婿)怎样?」
「他回答妳的问题说得对吗?」
「他懂不懂啊?」
于姐要监视他又要炫耀他。分手时,我们相约几天后在金门大桥边的克莱西沙滩会合,去看美国独立节烟花秀。到了放烟花那天,沙滩上挤满了人,都是一个个年轻力壮,我正发愁何处去找他们俩,远远便看见奥莱瑞一手高举拐杖,向我挥舞着,像个顽童。
犹记那夜璀璨的星空,伴随着金门大桥黑色的剪影,正从他俩的背后升起。如今,世事骤变,若再相约,又当在哪年哪月,何时何地呢?
(陈少聪,美国爱荷华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出版作品有《水莲》、《女伶》、《捕梦网》、《航向爱琴海》、《永远的外乡人》等。)
-
 典萃55瓶玻尿酸,秋冬补水快人一步,绽现水光肌!2020-09-25随着秋意逐渐转浓,天气变干,冷空气来袭,不仅人的抵抗力降低,肌肤的抵抗力其实也会变差,容易出现干燥、缺水症状,严重时甚至会起皮、泛红、干痒,以及刺痛。因此,秋冬季节
典萃55瓶玻尿酸,秋冬补水快人一步,绽现水光肌!2020-09-25随着秋意逐渐转浓,天气变干,冷空气来袭,不仅人的抵抗力降低,肌肤的抵抗力其实也会变差,容易出现干燥、缺水症状,严重时甚至会起皮、泛红、干痒,以及刺痛。因此,秋冬季节 -
 优衣库时尚外套,六大款型,六种风格,让你开启不设限的出彩生活2020-09-24渐入深秋,优衣库2020秋冬时尚外套系列全面上新,六大款型,轻松穿出六种出彩风格:户外外套-活力不设限、牛仔外套-个性不设限、灯芯绒外套-摩登不设限、工装外套-率性不设限、西
优衣库时尚外套,六大款型,六种风格,让你开启不设限的出彩生活2020-09-24渐入深秋,优衣库2020秋冬时尚外套系列全面上新,六大款型,轻松穿出六种出彩风格:户外外套-活力不设限、牛仔外套-个性不设限、灯芯绒外套-摩登不设限、工装外套-率性不设限、西 -
 Re;BAK!韩国国民初恋孙艺珍都站台的洗发水,你Get了吗?2020-09-24对于国内的80、90后来说“孙艺珍”这个名字绝对是耳熟能详,作为同龄人孙艺珍的美貌和智慧以及在影视剧中成功塑造的多个形象,早已深入国人心中。尤其是现在年龄已
Re;BAK!韩国国民初恋孙艺珍都站台的洗发水,你Get了吗?2020-09-24对于国内的80、90后来说“孙艺珍”这个名字绝对是耳熟能详,作为同龄人孙艺珍的美貌和智慧以及在影视剧中成功塑造的多个形象,早已深入国人心中。尤其是现在年龄已 -
 星巴克秋季新品上市,巧用掌上生活App升杯畅饮2020-09-24凉风有信,一叶知秋。转眼间,夏天已悄然转身,一杯香气四溢的星巴克咖啡,既衬这初秋好时光,又有助于驱散潜藏的倦意。近日,招商银行信用卡与星巴克推出联合会员专属权益全新
星巴克秋季新品上市,巧用掌上生活App升杯畅饮2020-09-24凉风有信,一叶知秋。转眼间,夏天已悄然转身,一杯香气四溢的星巴克咖啡,既衬这初秋好时光,又有助于驱散潜藏的倦意。近日,招商银行信用卡与星巴克推出联合会员专属权益全新 - Dr.Jart+蒂佳婷天猫全明星计划线上粉丝见面会和吴世勋一起 理想生活就耀活力2020-09-222020年9月22日晚20:00,淘宝直播蒂佳婷直播间,蒂造肌肤健康纯净之美的Dr.Jart+蒂佳婷携手品牌中国地区形象代言人:韩国男子流行演唱组合EXO成员吴世勋,首场蒂佳婷天猫全明星计划
- 凯仕丽改写荒漠贫困宿命 《中国好声音》“重走”国民红酒光荣史2020-09-21荧屏上,进入第九季的《中国好声音》,IP魅力不减。近日,《2020中国好声音》台前幕后一行人走进了这一季节目的指定红酒品牌——凯仕丽,空降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凯仕
-
 AVON雅芳焕“新颜” 全面重塑品牌形象2020-09-18(中国,上海)2020年9月16日——源自纽约的AVON雅芳在品牌成立135周年之际,正式宣布推出Watch Me Now品牌焕新活动,启用全新品牌形象。Watch Me Now活动包含的视
AVON雅芳焕“新颜” 全面重塑品牌形象2020-09-18(中国,上海)2020年9月16日——源自纽约的AVON雅芳在品牌成立135周年之际,正式宣布推出Watch Me Now品牌焕新活动,启用全新品牌形象。Watch Me Now活动包含的视 -
 《明日之子》不仅带出这些才子,还帮百事带了货2020-09-18要说今夏最热的综艺名单,由百事可乐独家冠名的《明日之子》必须榜上有名!学员们可圈可点的亮眼表现和一路走高的人气,都向人们展示了年轻人对音乐纯粹的热爱。追溯过去,百
《明日之子》不仅带出这些才子,还帮百事带了货2020-09-18要说今夏最热的综艺名单,由百事可乐独家冠名的《明日之子》必须榜上有名!学员们可圈可点的亮眼表现和一路走高的人气,都向人们展示了年轻人对音乐纯粹的热爱。追溯过去,百 -
 jenny house水光精华气垫火爆热卖,含有3种玻尿酸,保湿不是事儿!2020-09-17作为女性最为常用的护肤品之一气垫,市面上在售的已经有成百上千种之多。同类品项如此之多,想要脱颖而出必须要有真本领,要有差异化的优势。来自韩国首尔时尚前沿江南清潭洞的
jenny house水光精华气垫火爆热卖,含有3种玻尿酸,保湿不是事儿!2020-09-17作为女性最为常用的护肤品之一气垫,市面上在售的已经有成百上千种之多。同类品项如此之多,想要脱颖而出必须要有真本领,要有差异化的优势。来自韩国首尔时尚前沿江南清潭洞的 -
 Dr.Jart+蒂佳婷修复新活系列全新第二代新品上市,敏感肌烦恼一扫而光2020-09-16随着环境的不同,敏感肌的定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当下,在病毒、口罩、微尘雾霾等刺激肌肤的恶劣环境之下,有些人的皮肤因为反复受到外部刺激,逐渐“疲惫”,重复出现敏感
Dr.Jart+蒂佳婷修复新活系列全新第二代新品上市,敏感肌烦恼一扫而光2020-09-16随着环境的不同,敏感肌的定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当下,在病毒、口罩、微尘雾霾等刺激肌肤的恶劣环境之下,有些人的皮肤因为反复受到外部刺激,逐渐“疲惫”,重复出现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