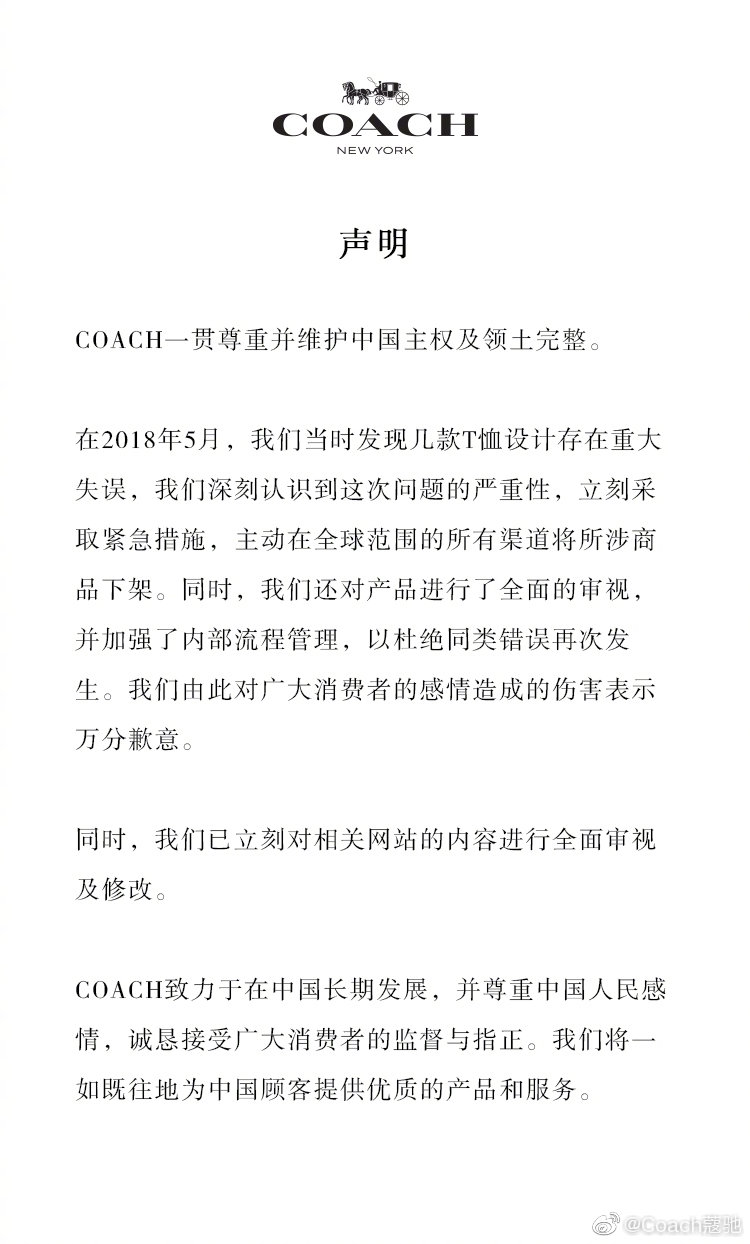一类的文革风云遭遇
一九六五年工作组进校,按桃园经验把全校教职工分成四类,一类是扎根对象,二类是依靠对象,三类是有严重问题的人,四类是革命斗争对象。其中一类,全校一百多教工经严格考察只留下二
一九六五年工作组进校,按桃园经验把全校教职工分成四类,一类是扎根对象,二类是依靠对象,三类是有严重问题的人,四类是革命斗争对象。
其中一类,全校一百多教工经严格考察只留下二人,其中一人解放前十四岁进资本家工厂当童工,解放后在本校初中毕业,入了党,留校当档案管理员,出身苦大仇深;但是她的丈夫后来提拔成某农村初中书记,文革时当然是走资派,只能排除在外。另外一人家庭是上中农,师大政教系毕业,当时是本校政治教师、党员;虽然不是响当当的贫雇农,也只能矮子里面选将军了。
这位老师平时也很来事,人很活跃,会唱会跳,她的夫君是大学同学,当时在省党校当教师。她和我们老教师关系也不错,是我们党课学习召集人。
文革开始,这名政治教师嗅觉特别灵敏,教师集训会时大家排队打早饭,突然高音喇叭响起,表示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她立即跳上旁边的水泥乒乓球台,边歌边舞边用秦腔的调门欢呼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她这一举动突显她是全校最最革命的形象,给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随后一段时间,她支持革命小将,一起去北京串联,成了红卫兵的军师。他们在北京看见红卫兵造反,把胡耀邦当条狗牵进牵出批斗,回到学校依法炮制,公布「点鬼」大字报,把全部四类和部分划成三类的教学骨干全点成鬼,暗示大家去批斗。
这位一类老师也成了造反派筹委会的副主任,正主任是红卫兵小将,大小事由她拿主意,成了事实上的新校长,可谓威风不可一世。
暑假到了,我因为老家的老人患病,要回家探望,就到掌权的筹委会请假,正好看见她就坐在原来校长办公室的圈椅上,翘着二郎腿。那把圈椅原来是一九五八年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时,木工组学生试制的产品,向党支部报喜后,放在仓库里埋没了学生的成绩,于是就留在校长办公室里,老校长就当办公座椅,有客人来顺便介绍一下。文革开始,这张椅子成了老校长贪图享受的罪状一条,想不到革命筹委会的新领导别无二致,照样享受不误。
这名一类教师进一步把反造到市上去,率领红卫兵包围市委,声称市委书记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揪市委书记。那位书记文化水平不高,做报告时提到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外国名字他念起来拗口,说成是「那个麦克啊,诺马拉」,当然辩不过我们的政教系毕业老师。这一新闻很快登上北京的造反小报,她的名声大振。不久后,这名一类教师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听说能够去那里学习,就是进入未来省市领导接班人的梯队。一时这位老师锋头之健,无出其右。
文革风云变幻无常,突然四人帮终结了, 老干部官复原职,原来划定的四类整死几个,但没有一个是真反革命,只是历史问题,而且都是交代清楚的。对文革造反英雄,当时有种普遍看法,凡是造反起家和投靠四人帮的一律不能重用,而且一市之内,每人几斤几两互相都知根知底。
重起的老干部对我们那位锋头很健的一类耿耿于怀,反覆地查来查去,这名教师最后被调到党校和她丈夫一起当个普通教员,前途发展无望。也许是上去容易下来难,由青云跌落尘埃,他们夫妻俩一直郁郁寡欢;不久,男的先离开了世界,我们的一类则慢慢精神失常,不过没有大疯大癫,只是一个人终日闷坐,沉思默想,不言不语。
夫妻俩也没有儿女,收养了一个女儿,这时当了工人,吃饭时,养女给她盛好饭,上面放些菜,她会独自在角落里把饭吃完。大家也把她遗忘了,过了几年,人们听说她也上了天堂,找她丈夫去了。大家对她的一生看法一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昙花一现,一生就过去了。
-
 扎根护肤市场7年,典萃终于迎来高光时刻2020-11-13在科技类、功能型护肤品需求日趋增加的当下,许多美妆品牌都开始探索科技护肤这片红海。典萃作为上海家化旗下的美妆护肤品牌,历经7年探索和沉淀,于2020年成功升级,正式对外
扎根护肤市场7年,典萃终于迎来高光时刻2020-11-13在科技类、功能型护肤品需求日趋增加的当下,许多美妆品牌都开始探索科技护肤这片红海。典萃作为上海家化旗下的美妆护肤品牌,历经7年探索和沉淀,于2020年成功升级,正式对外 -
 rorolove携手宋祖儿探索方寸之间的女性魅力2020-11-13她是《宝莲灯前传》里疾恶如仇的哪吒,她是九州缥缈录里美貌机智的羽然公主,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祖鹅”,她就是宋祖儿。近日,rorolove携手宋祖儿登上《NEUFMODE九号摩
rorolove携手宋祖儿探索方寸之间的女性魅力2020-11-13她是《宝莲灯前传》里疾恶如仇的哪吒,她是九州缥缈录里美貌机智的羽然公主,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祖鹅”,她就是宋祖儿。近日,rorolove携手宋祖儿登上《NEUFMODE九号摩 -
 业态创新 模式升级 Brand K直播带货迎战“双11”2020-11-1211月11日,电商平台“消费狂欢”高潮迭起。在这场“双11”购物盛宴中,Brand K以新兴业态“网红直播带货”的方式,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多品类
业态创新 模式升级 Brand K直播带货迎战“双11”2020-11-1211月11日,电商平台“消费狂欢”高潮迭起。在这场“双11”购物盛宴中,Brand K以新兴业态“网红直播带货”的方式,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多品类 -
 1.28亿!碧生源打造双十一健康盛宴 瘦身C位好物全网热销2020-11-12上半年疫情封印,让2020下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来得更加猛烈。直播带货线上火热“种草”,好物应接不暇,全网都是停不下来的买买买。受疫情驱动和公众消费理念提升
1.28亿!碧生源打造双十一健康盛宴 瘦身C位好物全网热销2020-11-12上半年疫情封印,让2020下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来得更加猛烈。直播带货线上火热“种草”,好物应接不暇,全网都是停不下来的买买买。受疫情驱动和公众消费理念提升 -
 如何与年轻人沟通?自然堂开办“支流大学”强势出圈2020-11-11年轻人的身上藏着一股独一无二的力量,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与自我,就像一条奔涌向前、充满热情的支流。然而就是这样各有风彩的年轻人,却总是因这份独有的不同而陷入社会各界的
如何与年轻人沟通?自然堂开办“支流大学”强势出圈2020-11-11年轻人的身上藏着一股独一无二的力量,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与自我,就像一条奔涌向前、充满热情的支流。然而就是这样各有风彩的年轻人,却总是因这份独有的不同而陷入社会各界的 -
 博物馆奇妙夜 ——JI CHENG 2021SS“鲤花”系列发布即将上线2020-11-10当夜幕降临魔都的黄浦江畔,奇妙空间被神秘能量开启,2020年11月16日,一场艺术情境中的视觉感官盛宴即将在Teamlab无界美术馆上演,中国著名独立时装设计师吉承怀抱对艺术的热
博物馆奇妙夜 ——JI CHENG 2021SS“鲤花”系列发布即将上线2020-11-10当夜幕降临魔都的黄浦江畔,奇妙空间被神秘能量开启,2020年11月16日,一场艺术情境中的视觉感官盛宴即将在Teamlab无界美术馆上演,中国著名独立时装设计师吉承怀抱对艺术的热 -
 坚韧进化,自成风度!G-SHOCK MT-G系列演绎进无止境2020-11-06跨越指针转动的风尚型格,是理想与时间的经年对谈。创造超越潮流的硬朗表达,是男士魅力的铮铮信条。这一次,G-SHOCK将MT-G产品线再度升级进化,在MTG-B1000基础上,全新推出MT
坚韧进化,自成风度!G-SHOCK MT-G系列演绎进无止境2020-11-06跨越指针转动的风尚型格,是理想与时间的经年对谈。创造超越潮流的硬朗表达,是男士魅力的铮铮信条。这一次,G-SHOCK将MT-G产品线再度升级进化,在MTG-B1000基础上,全新推出MT -
 双十一必buy清单 飘柔让秋冬护发尽享柔顺体验2020-11-05又逢双十一,你是否已经摩拳擦掌,做好准备买买买了?在绞尽脑汁计算凑单优惠的时候,肯定也在默默蹂躏自己的头发。说到头发护理,做好清洁是最基础的,但天气渐冷,正逢没有暖气的保护,
双十一必buy清单 飘柔让秋冬护发尽享柔顺体验2020-11-05又逢双十一,你是否已经摩拳擦掌,做好准备买买买了?在绞尽脑汁计算凑单优惠的时候,肯定也在默默蹂躏自己的头发。说到头发护理,做好清洁是最基础的,但天气渐冷,正逢没有暖气的保护, -
 优衣库携+J首次亮相进博会,演绎当代科技极简美学2020-11-052020年11月5日至10日,全球知名服饰品牌优衣库惊艳亮相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1500平方米“明日博物馆”。这是优衣库LifeWear全球品牌博览会继纽约、
优衣库携+J首次亮相进博会,演绎当代科技极简美学2020-11-052020年11月5日至10日,全球知名服饰品牌优衣库惊艳亮相上海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1500平方米“明日博物馆”。这是优衣库LifeWear全球品牌博览会继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