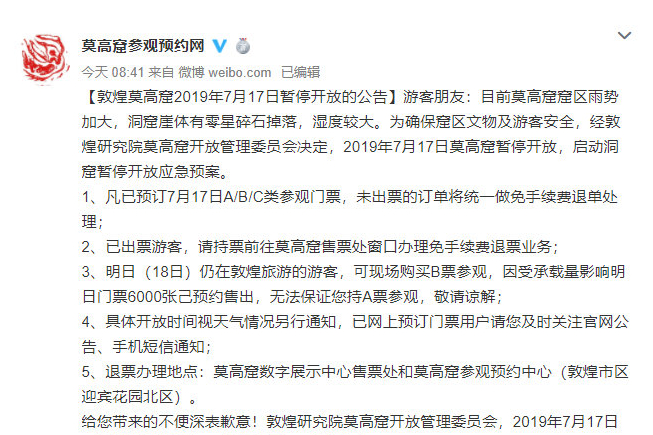蝉声缥缈
今年五、六月间的一天,偶在报刊一角读到一则新闻,说有某种周期蝉今年即将破土而出,它们群起而放声鸣叫,所形成的噪音可能会引起人们不适。记得当时我心头掠过一丝疑惑:美国也有
今年五、六月间的一天,偶在报刊一角读到一则新闻,说有某种周期蝉今年即将破土而出,它们群起而放声鸣叫,所形成的噪音可能会引起人们不适。记得当时我心头掠过一丝疑惑:美国也有蝉吗?我居北美近四十载,似乎从未见过,也几乎从不曾读到关于蝉的消息。
经过搜索,才知原来这周期蝉是美利坚独有。它们潜藏在东岸地区的土壤底下,度过悠长的十七年后,才渐渐成长、破土、羽化、交配、产卵、死亡,故称之为十七年蝉。今夏适逢一个发育周期结束,成虫将会从美东大片地域出来见世面。这种蝉不会螫咬人类,但会发出高达九十分贝的鸣声,据说等同于一台果汁机运作的声音。它们在十分漫长的发育周期后,才同时大量涌现的现象,数世纪以来,科学家仍未全盘了解其中奥秘。
这种蝉的生命型态令我惊叹不已,住在美西的我未曾见过它们,但能想像它们蛰伏地底多年,被沉厚滞重的土壤覆盖,与幽深冰冷的永夜相守,在黑暗沉寂的淤泥中漫长地等待……终于突破时间与空间的捆绑,拔地而起、奔向天光。由卵到蝉的过程绵长如许,成熟后的生命却那样短暂,只能活二至四周。成蝉飞上高枝,在重重密叶间倾泻嘹亮的嘶鸣,似乎要将过去多年的压抑全然释放,也要使出浑身解数,用尽能量,以不负此生……。
这番感悟掀动我记忆的深潭,想起蝉声罗织的岛乡岁月,以及蝉鸣贯串的童年夏天。台湾的蝉与北美的十七年蝉不同,从幼虫到成虫,需一年至五年时间,因此每年夏季都可见芳踪,听闻响彻街头巷尾的蝉唱。
记得幼时,我们把蝉叫做「知了」。知了知了,知道夏天来了。稚童们不由得兴奋起来,因为知了开始叫,就代表快要放暑假了。暑假期间,妈妈比较能容许我和小伙伴们出去嬉游。我家门前即是绵延至天际的田畦,大片稻海翻腾着翠浪金波,周遭竹篁展现诱人的葱绿,池塘中窜出亭亭玉立的红莲。伙伴们沿着乡间小路,蹦蹦跳跳进入树林,吆喝着去捕蝉。玩得大汗淋漓地回家,妈妈也不会板起脸来斥责,反而会递上一盘冰镇鲜果。水莲飘香,蝉鸣贯耳,草笠蒲扇,浮瓜沉李,构成一幅至今难忘的夏日童趣图。
求学时代我喜欢阅览文史,曾读到《礼记》的一段记述:「夏至到,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蝉声初响,木槿盛开,夏至翩然而来。原来蝉鸣、花开、鹿角脱落等自然现象都昭示了一种四季节气与生命礼节。亦体认到,华夏民族对于蝉是充满倾慕之情的——沉藏地底,潜心静修,苦候蜕变,征逐光明。缘此,佛家的禅与蝉同音,人们更视之为至德之虫。蝉与缠亦同音,在腰间配戴蝉形挂饰,寓意正是富贵吉祥的腰缠万」。
大学时去国文系旁听乐府诗,从此爱上了古典诗词,也了解到历代咏蝉的诗章多达数百篇。其中初唐名臣虞世南的一阕〈蝉〉诗最受称道: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意思是说啜饮清露的蝉,因为栖于高枝,鸣声自可远传,无须风力推波助澜。此诗以蝉喻人,内涵清越、秉性高洁之士,自能声名远播,是不需要攀龙附凤的。
我也喜爱宋朝辛弃疾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穿行明月清风里,忽闻鸣蝉;浸浴稻花禾香中,蛙声入耳,太平年月的丰景跃然纸上!
白居易〈早蝉〉诗的字里行间,却略带感伤:「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楠深叶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漫步江头听蝉鸣,油然心生故园情,乡愁总是催人早生华发……。
暑气方浓的盛夏,长风剪不断的蝉鸣,有时不免惹人心绪浮荡,此时展卷吟读清代名家纳兰性德的〈蝶恋花〉: 露下庭柯蝉响歇。纱碧如烟、烟里玲珑月。蝉响初歇,烟月玲珑的意境,仿佛能在炎夏中予人一掬清凉。
而今,童年捕蝉的身影早已遥不可追,吟风弄月、咏叹蝉诗的春华岁月亦飘然远逝。离家去国后,栖居大洋彼岸的异地,无论是庭蝉、早蝉、夜蝉还是寒蝉,俱已睽违多时。即使返乡探访,因多半避开盛暑,蝉鸣亦未闻久矣!此时此际,蝉声已渺、蝉踪难觅,然记忆不老,那纤薄蝉翼的金色幽芒,始终不渝地辉映在生命的霞光中。
-
 跟着时尚达人学穿搭,天冷,也能美的纤细,CARNAVAL DE VENISE你的秋冬时尚法宝2020-11-27在时尚圈,穿衣品味是展示一位女人魅力最直观的方式之一,不知道你们发现没,那些精致的女人们总能敏锐的抓住时尚的风向标,稳稳的站在时尚风口,就连在秋冬季,他们也能美的那么纤细
跟着时尚达人学穿搭,天冷,也能美的纤细,CARNAVAL DE VENISE你的秋冬时尚法宝2020-11-27在时尚圈,穿衣品味是展示一位女人魅力最直观的方式之一,不知道你们发现没,那些精致的女人们总能敏锐的抓住时尚的风向标,稳稳的站在时尚风口,就连在秋冬季,他们也能美的那么纤细 -
 CARNAVAL DE VENISE新作,彰显个性与复古的完美融合,重塑老花经典2020-11-27一向以“腿精”出圈的鲍蕾、贝儿母女最近又美出了新高度,不过不是因为美腿,而是因为一件复古小面具老花单品——CARNAVAL DE VENISE(威尼斯狂欢节)。 CAR
CARNAVAL DE VENISE新作,彰显个性与复古的完美融合,重塑老花经典2020-11-27一向以“腿精”出圈的鲍蕾、贝儿母女最近又美出了新高度,不过不是因为美腿,而是因为一件复古小面具老花单品——CARNAVAL DE VENISE(威尼斯狂欢节)。 CAR -
 佰草集典萃玻尿酸水润精华液,水光溢出看得见2020-11-26尽管很多女性都深知肌肤补水的重要性,但有些人就算不停补水,皮肤依旧缺水。所以,只有能够高效补水的护肤品,才能获得消费者垂青,以及被不断回购。 全新升级的典萃品牌,创研运
佰草集典萃玻尿酸水润精华液,水光溢出看得见2020-11-26尽管很多女性都深知肌肤补水的重要性,但有些人就算不停补水,皮肤依旧缺水。所以,只有能够高效补水的护肤品,才能获得消费者垂青,以及被不断回购。 全新升级的典萃品牌,创研运 -
 备战年底囤货季,拉多芮彩妆什么值得买?2020-11-26年底一向都是各种打折季,特别适合买买买,尤其是各种精美的彩妆。不管送人还是自用都是不会出错的选择,特别是法式生活典范——LM Laduree蕾美缪思拉多芮这种颜值
备战年底囤货季,拉多芮彩妆什么值得买?2020-11-26年底一向都是各种打折季,特别适合买买买,尤其是各种精美的彩妆。不管送人还是自用都是不会出错的选择,特别是法式生活典范——LM Laduree蕾美缪思拉多芮这种颜值 -
 #Back Together# ba&sh闺蜜相伴,派对永不落幕2020-11-26来自法国巴黎的时装品牌ba&sh自2003年创立以来,一直主力设计和生产全线女装系列,不仅为全球女性打造“理想衣橱”,更向她们传递积极向上的女性力量。2020年,ba&s
#Back Together# ba&sh闺蜜相伴,派对永不落幕2020-11-26来自法国巴黎的时装品牌ba&sh自2003年创立以来,一直主力设计和生产全线女装系列,不仅为全球女性打造“理想衣橱”,更向她们传递积极向上的女性力量。2020年,ba&s -
 坚韧不改,经典重燃!G-SHOCK AW-500系列复古回归2020-11-25复古回潮势头正夯,这不仅是一场潮流的重燃,更是对经典的致敬与重构。那些历经时间打磨的坚韧型格,正以夺目之势重返大众视野!时隔多年,G-SHOCK升级推出初代双显型号腕表A
坚韧不改,经典重燃!G-SHOCK AW-500系列复古回归2020-11-25复古回潮势头正夯,这不仅是一场潮流的重燃,更是对经典的致敬与重构。那些历经时间打磨的坚韧型格,正以夺目之势重返大众视野!时隔多年,G-SHOCK升级推出初代双显型号腕表A -
 “黑五”接棒双11 韩国线上商品周展好物“降”临2020-11-2511月22日,由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携旗下众多美妆护肤产品,再次登陆韩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韩国线上商品周展(以下简称“商品周展”),这也是该直播活动成
“黑五”接棒双11 韩国线上商品周展好物“降”临2020-11-2511月22日,由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携旗下众多美妆护肤产品,再次登陆韩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韩国线上商品周展(以下简称“商品周展”),这也是该直播活动成 -
 K11打造大湾区突破性零售餐饮娱乐地标项目 “11 天空”2020-11-24今天,K11集团宣布由新世界发展斥资200亿港元承建、坐落于香港国际机场SKYCITY航天城的世界级綜合商业项目正式命名为“11 天空” (“11 SKIES”)。K11
K11打造大湾区突破性零售餐饮娱乐地标项目 “11 天空”2020-11-24今天,K11集团宣布由新世界发展斥资200亿港元承建、坐落于香港国际机场SKYCITY航天城的世界级綜合商业项目正式命名为“11 天空” (“11 SKIES”)。K11 -
 有了这款Smiley粉底,瞬间变成整条gai最靓的姐!2020-11-24本人坐标首都,国庆期间逛津梁生活北京荟聚店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Smiley美妆的专柜。想到刚好要买粉底液了,于是精挑细选买了一瓶Smiley柔雾凝时精华粉底液。用了一段时间之
有了这款Smiley粉底,瞬间变成整条gai最靓的姐!2020-11-24本人坐标首都,国庆期间逛津梁生活北京荟聚店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Smiley美妆的专柜。想到刚好要买粉底液了,于是精挑细选买了一瓶Smiley柔雾凝时精华粉底液。用了一段时间之 -
 Unique Time与新加坡屈臣氏达成战略合作2020-11-24据悉,最近新加坡屈臣氏迎来了一名“新成员”—— Unique Time源萃果饮,一款天然健康的营养产品。Unique Time(简称UT)与屈臣氏达成的战略合作为消费者
Unique Time与新加坡屈臣氏达成战略合作2020-11-24据悉,最近新加坡屈臣氏迎来了一名“新成员”—— Unique Time源萃果饮,一款天然健康的营养产品。Unique Time(简称UT)与屈臣氏达成的战略合作为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