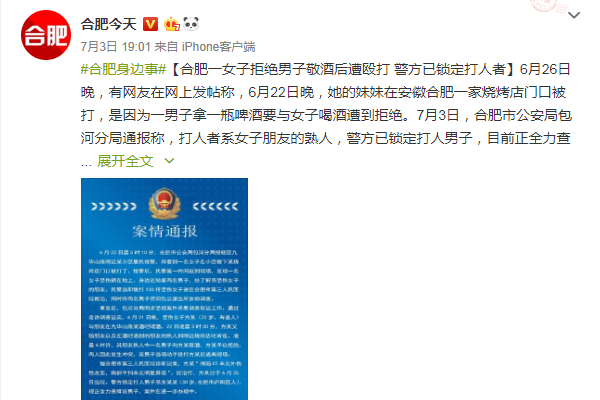童年往事
回想起来,已经是一甲子多的童年往事了。小时候住在台北南端,靠近新店溪的厦门街,当地的老居民还按照日据时代的称呼,叫作川端町。这里有相当一片范围是日本高级公务员的宿舍,木
回想起来,已经是一甲子多的童年往事了。小时候住在台北南端,靠近新店溪的厦门街,当地的老居民还按照日据时代的称呼,叫作川端町。这里有相当一片范围是日本高级公务员的宿舍,木结构的房子基本都是独门独院,有围墙相隔,前庭种些花木,颇为雅致。我们家在街上搬过三次,先是四十五巷的一栋日本榻榻米老房子,后来住进八十二巷改造式的日本房子,前后都有院子,宽敞得多,格局依旧是日式,有着进屋就要脱鞋的玄关与隔开空间的拉门,榻榻米却全部换作桧木地板,走在屋里咚咚有声,与天花板上猫捉老鼠的声响相映成趣。最后搬到一百一十三巷高墙大院的花园洋房,围墙种了一排龙柏与杂木,墙内有一片两三千呎的草坪,一条水泥铺的小道,蜿蜒通向掩映在第二排龙柏之后的住宅,是一栋五室两厅的西式洋房,正房后面有厨房浴室以及佣人房。据说原本是园林实验所的别墅,不知如何就变卖给我们了,住起来倒有些大隐隐于市的意味。
厦门街的南端尽头是河堤,横跨在溪上有道单行可通汽车的川端桥,后来改名中正桥,过桥就是永和,是通往板桥的干道。因此,厦门街是台北南端的通衢,商店云集,有座相当气派的警察局,有文具店、布店、饭铺、冰果室,还有远近驰名的开诚豆浆店。八十一巷是这一带重要的菜市场,巷口有几家鱼档,特别是卖鳝鱼与田鸡的一家,总是人头扰攘。主妇提着菜篮张望,小孩推挤向前,都在看那个小伙子把鳝鱼钉在俎板上,舞动利刃在鳝鱼背上划了一道,呲溜一声就把黏滑的鱼皮扒个干净,露出细白的肉身。再转过来一刀,开肠剖肚,一刮一甩,大功告成。对付田鸡的手法相同,也是一钉、一划、一扯,翻过来一刀、一刮,完事。他身手俐落,工作时间不长,两大盆黄鳝、两网兜青蛙,一早上就卖光了,冲洗了地摊的路面,清清爽爽走人。我有时就想,那小子额头系着青巾,刀法又快又准,俐落得像风吹树梢,颇有点宫本武藏的气势,应该是庖丁解牛一脉相承的,不知道是否隐在市场里的侠客。
厦门街中段有座萤桥,据说昔日因为地势低洼,草木丛生,到晚上就有无数萤火虫聚集,上下飞舞,因而得名。萤桥西北侧有一块相当辽阔的空地,旁边还有座小庙,每到祭祀的节日,就搭起戏棚唱布袋戏。我们挤在人群里看戏,喜欢锵锵哐哐的武打场面,看那些掌中的人偶居然打得鸡飞狗跳,舞刀动枪,很有些关公战秦琼的模样。其实,看戏并不是我们最向往的,最吸引我们这些孩子的,是赶集卖春饼的小贩,推着一车切成细丝的食材,有萝卜丝、胡萝卜、包心菜、绿豆芽、韭菜、黄瓜,或许还有点肉丝,堆积如山,在煤气灯贴上红遮板的映照下,如此吊人胃口。摊开薄薄的春饼,铺上杂拌的食料,洒上花生粉,抹上甜辣酱,卷起来,一口咬下去,哎呀,真是胜过山珍海味,美妙芳香不可言。
萤桥稍稍偏南,有一条从新店到万华(艋舺)的火车线路,横穿厦门街而过,车辆行人时常得站在放下的栏杆边上,等着呼哧呼哧的小火车从远方,冒着浓浓的黑烟蹒跚而来。街西有座萤桥火车站,乘车得买票进站,好像是五毛钱还是一块,记不得了。我们时常绕过入口,从旁边民居混入车站月台,搭一趟免费的顺风车。在火车开动不久,检票员走过来之前,就跳车逃窜,也算是儿时冒险犯难的伟大事迹。
在铁道南边,有条平行的诏安街,一直往西走,就是我的小学,萤桥国小。进了学校,我们都是乖乖的小学生,不怎么捣乱的。
-
 跟着时尚达人学穿搭,天冷,也能美的纤细,CARNAVAL DE VENISE你的秋冬时尚法宝2020-11-27在时尚圈,穿衣品味是展示一位女人魅力最直观的方式之一,不知道你们发现没,那些精致的女人们总能敏锐的抓住时尚的风向标,稳稳的站在时尚风口,就连在秋冬季,他们也能美的那么纤细
跟着时尚达人学穿搭,天冷,也能美的纤细,CARNAVAL DE VENISE你的秋冬时尚法宝2020-11-27在时尚圈,穿衣品味是展示一位女人魅力最直观的方式之一,不知道你们发现没,那些精致的女人们总能敏锐的抓住时尚的风向标,稳稳的站在时尚风口,就连在秋冬季,他们也能美的那么纤细 -
 CARNAVAL DE VENISE新作,彰显个性与复古的完美融合,重塑老花经典2020-11-27一向以“腿精”出圈的鲍蕾、贝儿母女最近又美出了新高度,不过不是因为美腿,而是因为一件复古小面具老花单品——CARNAVAL DE VENISE(威尼斯狂欢节)。 CAR
CARNAVAL DE VENISE新作,彰显个性与复古的完美融合,重塑老花经典2020-11-27一向以“腿精”出圈的鲍蕾、贝儿母女最近又美出了新高度,不过不是因为美腿,而是因为一件复古小面具老花单品——CARNAVAL DE VENISE(威尼斯狂欢节)。 CAR -
 佰草集典萃玻尿酸水润精华液,水光溢出看得见2020-11-26尽管很多女性都深知肌肤补水的重要性,但有些人就算不停补水,皮肤依旧缺水。所以,只有能够高效补水的护肤品,才能获得消费者垂青,以及被不断回购。 全新升级的典萃品牌,创研运
佰草集典萃玻尿酸水润精华液,水光溢出看得见2020-11-26尽管很多女性都深知肌肤补水的重要性,但有些人就算不停补水,皮肤依旧缺水。所以,只有能够高效补水的护肤品,才能获得消费者垂青,以及被不断回购。 全新升级的典萃品牌,创研运 -
 备战年底囤货季,拉多芮彩妆什么值得买?2020-11-26年底一向都是各种打折季,特别适合买买买,尤其是各种精美的彩妆。不管送人还是自用都是不会出错的选择,特别是法式生活典范——LM Laduree蕾美缪思拉多芮这种颜值
备战年底囤货季,拉多芮彩妆什么值得买?2020-11-26年底一向都是各种打折季,特别适合买买买,尤其是各种精美的彩妆。不管送人还是自用都是不会出错的选择,特别是法式生活典范——LM Laduree蕾美缪思拉多芮这种颜值 -
 #Back Together# ba&sh闺蜜相伴,派对永不落幕2020-11-26来自法国巴黎的时装品牌ba&sh自2003年创立以来,一直主力设计和生产全线女装系列,不仅为全球女性打造“理想衣橱”,更向她们传递积极向上的女性力量。2020年,ba&s
#Back Together# ba&sh闺蜜相伴,派对永不落幕2020-11-26来自法国巴黎的时装品牌ba&sh自2003年创立以来,一直主力设计和生产全线女装系列,不仅为全球女性打造“理想衣橱”,更向她们传递积极向上的女性力量。2020年,ba&s -
 坚韧不改,经典重燃!G-SHOCK AW-500系列复古回归2020-11-25复古回潮势头正夯,这不仅是一场潮流的重燃,更是对经典的致敬与重构。那些历经时间打磨的坚韧型格,正以夺目之势重返大众视野!时隔多年,G-SHOCK升级推出初代双显型号腕表A
坚韧不改,经典重燃!G-SHOCK AW-500系列复古回归2020-11-25复古回潮势头正夯,这不仅是一场潮流的重燃,更是对经典的致敬与重构。那些历经时间打磨的坚韧型格,正以夺目之势重返大众视野!时隔多年,G-SHOCK升级推出初代双显型号腕表A -
 “黑五”接棒双11 韩国线上商品周展好物“降”临2020-11-2511月22日,由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携旗下众多美妆护肤产品,再次登陆韩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韩国线上商品周展(以下简称“商品周展”),这也是该直播活动成
“黑五”接棒双11 韩国线上商品周展好物“降”临2020-11-2511月22日,由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携旗下众多美妆护肤产品,再次登陆韩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韩国线上商品周展(以下简称“商品周展”),这也是该直播活动成 -
 K11打造大湾区突破性零售餐饮娱乐地标项目 “11 天空”2020-11-24今天,K11集团宣布由新世界发展斥资200亿港元承建、坐落于香港国际机场SKYCITY航天城的世界级綜合商业项目正式命名为“11 天空” (“11 SKIES”)。K11
K11打造大湾区突破性零售餐饮娱乐地标项目 “11 天空”2020-11-24今天,K11集团宣布由新世界发展斥资200亿港元承建、坐落于香港国际机场SKYCITY航天城的世界级綜合商业项目正式命名为“11 天空” (“11 SKIES”)。K11 -
 有了这款Smiley粉底,瞬间变成整条gai最靓的姐!2020-11-24本人坐标首都,国庆期间逛津梁生活北京荟聚店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Smiley美妆的专柜。想到刚好要买粉底液了,于是精挑细选买了一瓶Smiley柔雾凝时精华粉底液。用了一段时间之
有了这款Smiley粉底,瞬间变成整条gai最靓的姐!2020-11-24本人坐标首都,国庆期间逛津梁生活北京荟聚店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Smiley美妆的专柜。想到刚好要买粉底液了,于是精挑细选买了一瓶Smiley柔雾凝时精华粉底液。用了一段时间之 -
 Unique Time与新加坡屈臣氏达成战略合作2020-11-24据悉,最近新加坡屈臣氏迎来了一名“新成员”—— Unique Time源萃果饮,一款天然健康的营养产品。Unique Time(简称UT)与屈臣氏达成的战略合作为消费者
Unique Time与新加坡屈臣氏达成战略合作2020-11-24据悉,最近新加坡屈臣氏迎来了一名“新成员”—— Unique Time源萃果饮,一款天然健康的营养产品。Unique Time(简称UT)与屈臣氏达成的战略合作为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