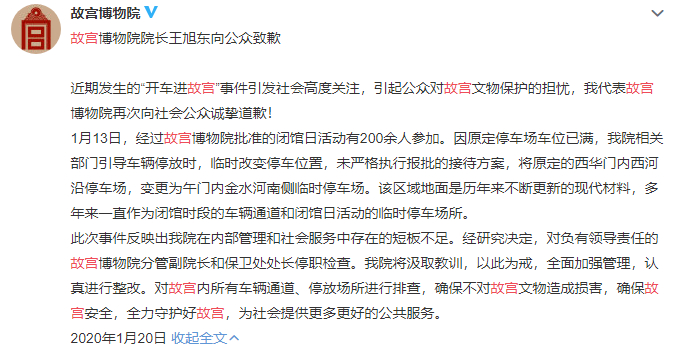弦歌不辍在战火中国(下)
离开南京整整一年后,我们来到了重庆。我体弱不能随中山中学前往川中,留在重庆进入南开中学,它的创办人张伯苓励志救国。1894年他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
离开南京整整一年后,我们来到了重庆。我体弱不能随中山中学前往川中,留在重庆进入南开中学,它的创办人张伯苓励志救国。1894年他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他悲愤填胸,深信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便毅然离开海军,办南开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七月二十八日天津南开即被日军飞机炸毁,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迁往昆明成为西南联大。南开中学在重庆沙坪坝重建,成为战时最好的中学。
抗战八年,张校长时时鼓励国人志气的演讲中国不亡,有我!就是我服膺一生的南开精神。
在那个时代,没有传播的设备,南开在战时是全体住校管理的,高、初中部和女生部校区散开,各据一方,上下课全是由军号宣示。这么多年来,我仍常在蒙蒙亮的冬日早晨,在半睡半醒之际,似乎听见那不容妥协、雄壮的起床号。
那些年,起床号后的人生,对所有人都是艰辛的。前线血战,重庆在日夜轰炸下颤栗,人人生死难卜,十六、七岁的我们实在很怕又很累,就抱怨数学老师功课太多,又不停小考,怎么活得了,老师伉乃如(我们称他「伉老二」)说:「你们整天瞪着天空看,想着炸弹掉下来,有用吗?天空有回答吗?做数学题和背国文、英文至少给自己脑袋留点东西。你们这么年轻,干瞪眼,甘心吗?」跑警报时,仍能让明天的功课分担死亡的威胁。
1945年2月,我二十岁,由全国大学联考分发到战时西迁的武汉大学哲学系(二年级转入外文系),在三江环绕合流注入长江的四川乐山,有缘修读朱光潜老师的英诗课。那古老的石砌文庙配殿就是我与蓝天间的一间密室,我们又读又背雪莱的〈云雀之歌〉和济慈的〈夜莺颂〉,随着老师的声音,心灵激荡,忘记了日渐逼近的炮火,直到被中庭钟声召唤,回到现实。校长王星拱在广场召集师生谈话,宣布重要消息:战事失利,日军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紧急时,由师管区保护,撤退进入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臞,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这之后七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最大的依靠。
方德万教授成长于荷兰,大学读中文,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现代史,受聘英国剑桥大学教书,已经用了三十年写中国现代战争史,在这四种文化氛围中看世事,他有更大视野。他在本书导论所述,1940年纳粹占领了荷兰,他的外祖父是个小镇上受尊重的进口商,德国人指控他藏匿武器,把他关押,战争将结束时,把他送到德国,他在被美军救出后几天就病死在东德。两德统一后,2014年方教授和他的家人循着外祖父逃亡的路线,来到东德他最后来信的城,但是找不到他葬身何处。在他的孙子和他们的后代心中,他未得安葬,也许就如中国传统上所说,成了游荡异乡的孤魂了吧!也许正是因此,他用一整页写重庆迎灵路祭张自忠将军的悲恸。
他在学术研究中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伤亡数千百万军民,捐躯卫国,战后却多数未能归葬乡里。1949之后,生者无言,死者默默,写史之际,岂止感到悲悯与同情而已。
在为这本集大成之作的台湾版序中他说这是一本:「真正为自己而写……非常私人的书……研究中国抗战成为我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结束后的伤痛的遗留的方法,这个主题始终萦绕,让我无法放手。」序末说:「以此为出发点,关照引人入胜战争记忆的跨世代传承以及沉默的课题;这些课题对中国背景逐渐退去的台湾而言非常重要。」他这似轻轻提起的「沉默」二字,在我听来,却是震耳欲聋,摧心悲痛。沉默和遗忘使青史成灰,是死者第二次死亡。幸好历史是一个倔强的存在,不容被盖棺,也不容被论定。
我这篇小小的书中人语,暮年心绪,竟从惊蜇、春分,写到清明。谷雨已过,我仍在迟疑徘徊,无法结语。七十年怅憾,说不尽对殉国军人及朋友的悼念与感恩。因为他们奋勇捐躯,国家得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也维持了弦歌不辍的民族希望。感谢方教授以感同身受的史家大悲悯,写活了那场战争中的关键岁月。(下)
-
 完美日记携手女性航天工作者,寻色宇宙星空,探索内心力量2020-11-30今年,是中国的航天元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顺利升空,将实现我国首次在月球表面采集土壤并返回地球。每一次的发射,都离不开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以及他们坚毅不拔的航天精神。而在
完美日记携手女性航天工作者,寻色宇宙星空,探索内心力量2020-11-30今年,是中国的航天元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顺利升空,将实现我国首次在月球表面采集土壤并返回地球。每一次的发射,都离不开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以及他们坚毅不拔的航天精神。而在 -
 Palilis闪亮登陆紫金国际美学医学联合大会完美演绎女性抗衰新路径2020-11-30日本知名女性私密抗衰品牌2020紫金国际美学医学联合大会暨2020第四届全国私密美学整形交流大会,由中国形美容协会医学美学设计与咨询分会主办,是中国私密行业为数不多的专
Palilis闪亮登陆紫金国际美学医学联合大会完美演绎女性抗衰新路径2020-11-30日本知名女性私密抗衰品牌2020紫金国际美学医学联合大会暨2020第四届全国私密美学整形交流大会,由中国形美容协会医学美学设计与咨询分会主办,是中国私密行业为数不多的专 -
 跟着时尚达人学穿搭,天冷,也能美的纤细,CARNAVAL DE VENISE你的秋冬时尚法宝2020-11-27在时尚圈,穿衣品味是展示一位女人魅力最直观的方式之一,不知道你们发现没,那些精致的女人们总能敏锐的抓住时尚的风向标,稳稳的站在时尚风口,就连在秋冬季,他们也能美的那么纤细
跟着时尚达人学穿搭,天冷,也能美的纤细,CARNAVAL DE VENISE你的秋冬时尚法宝2020-11-27在时尚圈,穿衣品味是展示一位女人魅力最直观的方式之一,不知道你们发现没,那些精致的女人们总能敏锐的抓住时尚的风向标,稳稳的站在时尚风口,就连在秋冬季,他们也能美的那么纤细 -
 CARNAVAL DE VENISE新作,彰显个性与复古的完美融合,重塑老花经典2020-11-27一向以“腿精”出圈的鲍蕾、贝儿母女最近又美出了新高度,不过不是因为美腿,而是因为一件复古小面具老花单品——CARNAVAL DE VENISE(威尼斯狂欢节)。 CAR
CARNAVAL DE VENISE新作,彰显个性与复古的完美融合,重塑老花经典2020-11-27一向以“腿精”出圈的鲍蕾、贝儿母女最近又美出了新高度,不过不是因为美腿,而是因为一件复古小面具老花单品——CARNAVAL DE VENISE(威尼斯狂欢节)。 CAR -
 佰草集典萃玻尿酸水润精华液,水光溢出看得见2020-11-26尽管很多女性都深知肌肤补水的重要性,但有些人就算不停补水,皮肤依旧缺水。所以,只有能够高效补水的护肤品,才能获得消费者垂青,以及被不断回购。 全新升级的典萃品牌,创研运
佰草集典萃玻尿酸水润精华液,水光溢出看得见2020-11-26尽管很多女性都深知肌肤补水的重要性,但有些人就算不停补水,皮肤依旧缺水。所以,只有能够高效补水的护肤品,才能获得消费者垂青,以及被不断回购。 全新升级的典萃品牌,创研运 -
 备战年底囤货季,拉多芮彩妆什么值得买?2020-11-26年底一向都是各种打折季,特别适合买买买,尤其是各种精美的彩妆。不管送人还是自用都是不会出错的选择,特别是法式生活典范——LM Laduree蕾美缪思拉多芮这种颜值
备战年底囤货季,拉多芮彩妆什么值得买?2020-11-26年底一向都是各种打折季,特别适合买买买,尤其是各种精美的彩妆。不管送人还是自用都是不会出错的选择,特别是法式生活典范——LM Laduree蕾美缪思拉多芮这种颜值 -
 #Back Together# ba&sh闺蜜相伴,派对永不落幕2020-11-26来自法国巴黎的时装品牌ba&sh自2003年创立以来,一直主力设计和生产全线女装系列,不仅为全球女性打造“理想衣橱”,更向她们传递积极向上的女性力量。2020年,ba&s
#Back Together# ba&sh闺蜜相伴,派对永不落幕2020-11-26来自法国巴黎的时装品牌ba&sh自2003年创立以来,一直主力设计和生产全线女装系列,不仅为全球女性打造“理想衣橱”,更向她们传递积极向上的女性力量。2020年,ba&s -
 坚韧不改,经典重燃!G-SHOCK AW-500系列复古回归2020-11-25复古回潮势头正夯,这不仅是一场潮流的重燃,更是对经典的致敬与重构。那些历经时间打磨的坚韧型格,正以夺目之势重返大众视野!时隔多年,G-SHOCK升级推出初代双显型号腕表A
坚韧不改,经典重燃!G-SHOCK AW-500系列复古回归2020-11-25复古回潮势头正夯,这不仅是一场潮流的重燃,更是对经典的致敬与重构。那些历经时间打磨的坚韧型格,正以夺目之势重返大众视野!时隔多年,G-SHOCK升级推出初代双显型号腕表A -
 “黑五”接棒双11 韩国线上商品周展好物“降”临2020-11-2511月22日,由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携旗下众多美妆护肤产品,再次登陆韩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韩国线上商品周展(以下简称“商品周展”),这也是该直播活动成
“黑五”接棒双11 韩国线上商品周展好物“降”临2020-11-2511月22日,由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携旗下众多美妆护肤产品,再次登陆韩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韩国线上商品周展(以下简称“商品周展”),这也是该直播活动成 -
 K11打造大湾区突破性零售餐饮娱乐地标项目 “11 天空”2020-11-24今天,K11集团宣布由新世界发展斥资200亿港元承建、坐落于香港国际机场SKYCITY航天城的世界级綜合商业项目正式命名为“11 天空” (“11 SKIES”)。K11
K11打造大湾区突破性零售餐饮娱乐地标项目 “11 天空”2020-11-24今天,K11集团宣布由新世界发展斥资200亿港元承建、坐落于香港国际机场SKYCITY航天城的世界级綜合商业项目正式命名为“11 天空” (“11 SKIES”)。K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