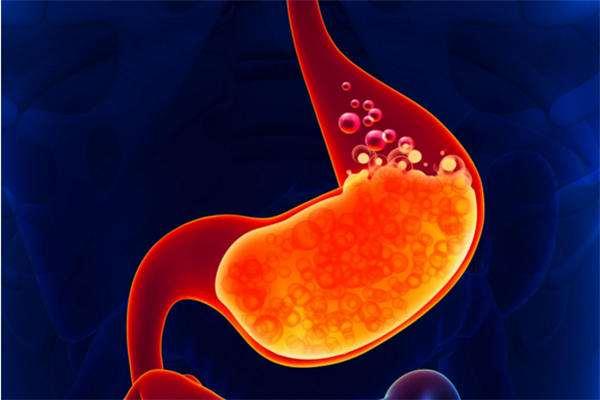那天下午树林里的雪,铺天盖地而来。
下午4点的斯德哥尔摩已经像是晚间,树影幢幢的树林里,没有人迹。几天前下过的雪在地上结了冰,她走在上面战战兢兢,害怕一个不留神便会滑倒。
天很阴沉。仿佛怀抱着的冰霜是一种浓浓厚厚的情绪。但她们不敢奢望,因为1月初的斯德哥尔摩不常下大雪。
走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她在小路的灯光里突然看到银光闪烁,小雪柔软地降向大地。
她前方走着两个瘦高的瑞典年轻男孩。她走在他们身后,一直在欣赏他们笔直的长腿。瑞典人大概从小在冰雪上行动,几乎都有修长完美的腿形。
突然他们两人半蹲在地,分别用手抓捏起雪球,往对方身上砸去。其中一个男孩一晃神滑了一跤,看她们走过,脸上有点不好意思的神情。
她们继续往草坪前方走去。经过路右边的一排苹果树。(没有叶子,都是光秃秃的枝桠。)她认不出是苹果树,是杉说的。
路过左边一栋亮着灯的房子。在冬日的寒冷里,那些窗户透着昏黄灯光的房子,形成她从小对家的最美好想象。
路过一匹匹在雪中吃草的漂亮马儿,看她们经过,纷纷探头过来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新鲜食物喂食。
向右拐,就是这片围绕着一个湖泊的树林。
“哦,这就是从你的宿舍窗口看到的湖泊。春天有白色天鹅戏水。”她对杉说。
绕过湖泊,在树林里,雪突然铺天盖地而来。
灯光下,雪花在风里转着圈子,随着窜动的气流表演着安静却又充满生命力的舞蹈。
她站在那里,让脸庞迎向风与飘雪。这正是她需要的。一场冰冷圣洁的来自那更高力量的力量。
雪花一点一点粘在她脸上,每一朵都微微地刺痛着她的神经。她的脸迅速地麻痹着,然后就再也感觉不到一朵朵的雪花,只是一片越来越强烈的冰冷在脸上凝聚蔓延。
照理说热能才是力量,从更热的物体流向温度较低的物体,现在她用自己的体温去融化每一朵雪花,她应该感觉自己的能量在一点一点消逝中。但是没有,她在雪里面开始亢奋。本来以为已经疲倦的身躯,本来有些灰蓝的心情,竟在雪花的消融中,被润湿、被滋养。像一瓣瓣逐渐舒展开来的花瓣儿。像一片清脆的冰蓝迅速伸延向远方。
在斯德哥尔摩,她第一次发现下雪原来是有声音的。
那是在城里的一场小雪。她站在房子的小阳台上,看她抵达以后的第一场雪。然后就听到“滋、滋、滋”的声音。很细微很轻柔,有着几乎不存在的空灵。就因为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那么安静,小阳台前方的庭院那么静止不动,才凸显出小雪的动态、小雪的声音。
从那么遥远的天空啊,凝结成那么圣洁晶莹的存在。在飞舞向大地的刹那,就已经知道结局将是消逝,请容许我发出一声叹息吧!在我用柔软的身躯触碰你坚硬的躯壳的当儿。在我放弃这圣洁晶莹的身躯,化入你坚硬的当儿……
雪花知道她的归宿吗?是小草?是河流?还是那座英俊雕塑的唇边?
她甘愿消失吗?她甘愿消失吧。
树林里的雪,一样的发出她细微、轻柔的叹息。
她站在那里感动不已。她们站在树林里抱成一团。
这是新的一年在大雪里的拥抱,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一天。2022年伊始,她们三个人有缘在大雪里拥抱彼此。
她们在大雪中、昏暗的天空下继续前行。迈过一个小山丘、一片平原、一个小农场、一片通往宿舍的空地,抵达一个车站。
那个地方有些荒凉,叫不到计程车。
她坐在车站里。马路过去是一棵老橡树。枝干向四方伸展出去,姿态很美丽。
那个更高的力量,显然是准备好了一场以老橡树为背景的风雪表演,硬是要她欣赏。她们等的计程车姗姗来迟,她只好在寒冷中,瑟缩在透明塑料车站的座位上,看前方的一场风雪。
尽管很冷,她不得不承认:真是美。真是壮观。真是迷人。(她可以感觉到那股神秘力量沾沾自喜的样子。)
大雪迅速地把马路变成一座白灰色的舞台。街灯下老橡树的黑色枝干,很快被白雪覆盖,镶上一层一层淡淡的银白。就像油画里描绘的一模一样。
她坐在那里30分钟,看那一棵橡树一点一点地被大雪上妆。银白色一点一点地增加,雪花疯狂地在她面前飘舞、旋转,再飘舞……
这真是一场向她炫耀生命力量的表演。她臣服于祂。
或许,这一次,她到斯德哥尔摩,不仅是因为她的女儿们。她仿佛,也更接近她生命的真相了。